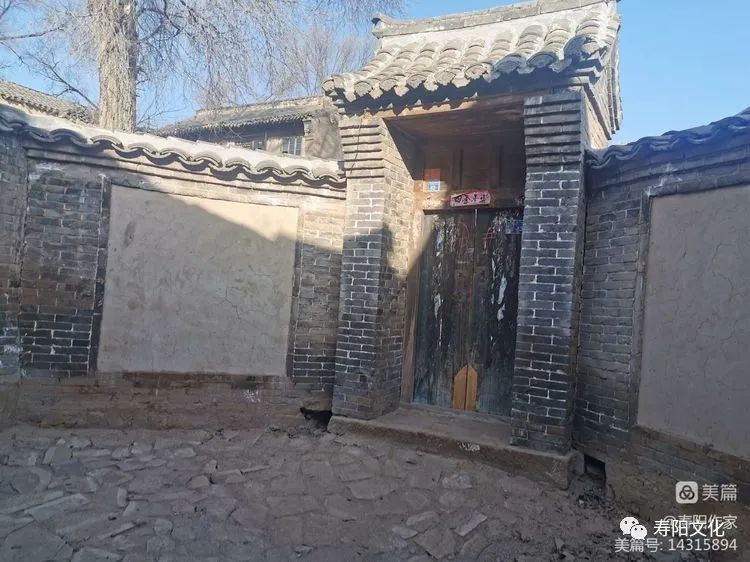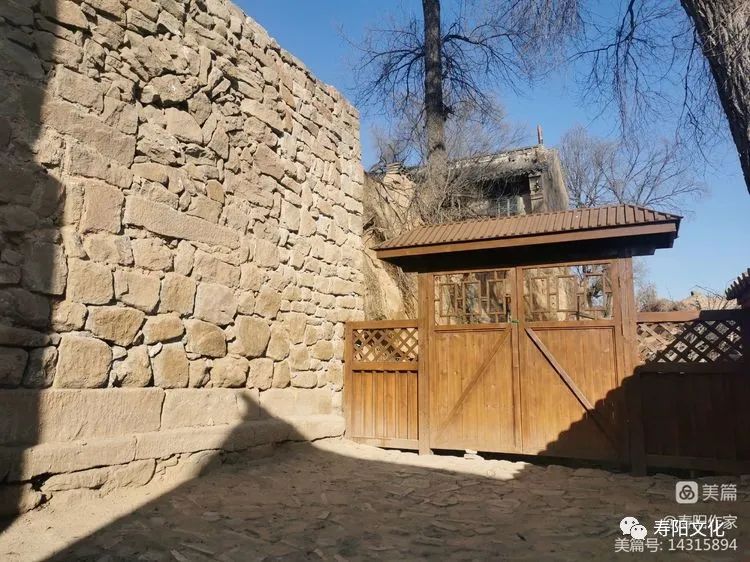乡村历史长卷 农耕文化缩影(三)
一一读《三晋契约》
文/郭春林
五是家族社会凝聚力强。历史以来,中国的社会,就是以家族为主,依靠宗法势力来加以统治。换句话说,就是官家对最基层的农村和农民,关注度相当低,交了皇粮自称王。这种乡村的治理,从行政力量上来看,是很松散的。人与人之间,以及家庭与家庭之间发生矛盾或纠纷,多数是依靠家长和族长来处理的。从本书收集的契约来看,也反映了这一点。无论是卖地还是卖房,主家首先想到的是先要卖给同族本家,其次才是卖给外姓人家。这样做的目的,一方面可以维护做人的尊严,因为卖祖上留下的产业,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情,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想迈出这一步。另一方面,还有着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的考虑。但是在动议阶段,往往是先要和长辈、同族的主事人商量,它所凸现出的是一种尊老敬贤的优良传统,也不排除恳求同族人来帮助走出困境的心理。可惜,在生产力发展极度低下,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的时代,大家只能是爱莫能助,所能给予的,也许仅仅是口头上的安慰而已。所以,从很多卖地契中看到的就是,“今情愿出卖于本家×××,永远耕种承业。”各种心酸,只有当事人清楚了。但是,涉及到分家契,就能看到,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和合文化,乃至于温良恭谦让的真正魅力了。

如,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初七,张家三兄弟分家契。开头就写明是:“敬承母命,无感违抗。”说明分家是老母亲提议做主的。接下来又写到:“念其家事大繁,人众费广,亲老气衰,理宜分饪。会请家属托天由命,和议分居。”这是在说明分家的理由,并且还请了长辈在场。让人感到当时的场面一定是既温馨又严肃。然后“将原置到房屋地产奉堂留用。有里松湾地六亩,以为养老死送之资,钱帛恭养,各志其孝,下余遗业按三股均分。”最后详细写清三兄弟应该得土地和院落数量,及其方位。在场的家属包括叔父、族兄、伯兄、族兄等。从中可看出,这是一户大户人家,家境殷实,母亲有威望,子女都孝顺,家庭和睦,治家有方,具有很强的凝聚力。尽管分家了,但是并没有分心。
六是契约精神严谨诚信。近年来,有学者认为,我们的国家以农业立国,小农经济,自给自足,没有交易,在很长时间内,是人情社会,缺乏契约精神。还有的甚至说,我们是熟人社会,人口流动性差,契约不起什么作用,其实,这实在是一种无误解。说穿了,是对历史的无知。
契约是文明起源的标志,是维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。如果我国缺乏契约精神,那又如何解释《三晋契约》一书中所收集的1194件契约?通读全书,让我们看到的,是我们这个民族具有很强的契约精神和自律意识。从这些契约当中,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前人办事是多么讲规矩,又是多么讲诚信。他们严谨认真,考虑周全,既有先小人后君子,好朋友清算账的自我约束,也还有买卖不成仁义在的雅量。
以706件清代契约为例,不管是家族后人均分祖坟的大小松树,还是买卖茅房粪池,大到地亩房屋,小到一桌一椅,都会在契约中写得清清楚楚。而且文末都有“恐口无凭,立此文约为证”的话语。有的还甚至要加上“永不反悔”,以示庄严慎重。数据之精确,令人咋舌。如清代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八范和礼分产契,写明“分地一亩六分二厘五毫,随带地纳原粮二斗四升三合七勺五毫。”土地面积精确到五毫,真不知道是怎么丈量和计算出来的。
之所以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缺乏契约精神,只是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,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,我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,军阀混战,广大农民深受其害,生产难以为继,生活极端贫困,官府只知盘剥,军阀只知害民,社会动荡不安,农村更加凋敝,人们精神滑坡所致,这也正是三座大山压迫的结果。但是,文化传承仍然在顽强地得以支撑,信用体系仍然没有坍塌。
道光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的买羊借钱契,就很能说明问题。立借约人王姓,因为买羊无钱,借到堂兄钱二十八千文,言明此钱无利息,只踩七月麦地一圈,有饭到小雪。回圈踩至来年清明节了粪尽。草喂羊无人工饭。
这件事如果放在现在实在是太简单了。不就是向堂兄借钱买羊,再让羊来踩粪顶利息嘛。还真的就根本不需要立什么契约。但是当年的双方就是这么认真。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可贵之处,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血脉所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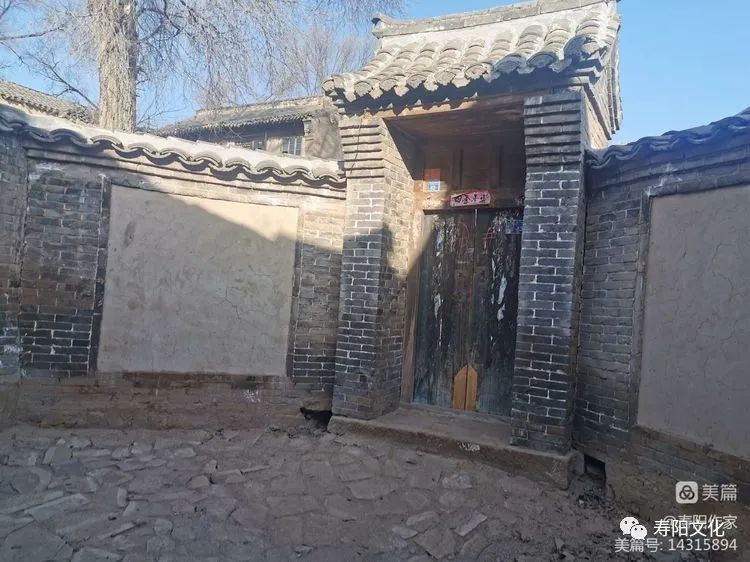
七是传统文化维系纽带。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,富有魅力已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是,这种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家庭的承载,从每个家庭成员身上体现出来的。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一书中曾指出,“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,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。如果事业小,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,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;如果事业大,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负担时,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庭里”。其特色是“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,在夫妇间得相敬,女子有着‘三从四德’的标准,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。”这就把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的特点讲得很清楚了。在以家族为主的乡村社会中,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,一个家族的几代人都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,人口流动慢,带来的必然是生活节奏慢。千百年的乡土文化积淀,日出而作,日落而歇,使得传统文化发挥到了极致。儒家文化的熏陶,庙宇香火的浸润,即使是一个文盲,他也会逐渐明白仁义礼智信的意义所在。所以,君子一言,驷马难追,一诺千金,诚实守信,早已经根深蒂固。但是,也有不怕一万,就怕万一的担忧。这个时候,道德的力量和人格的魅力就显得格外重要了。当道德的力量占据了乡村的制高点之后,传统的文脉,必然会释放出巨大的威力。表现在契约上就是,既要合情,又要合理。情,体现出的是亲情和乡亲之情,考虑到的是熟人社会里的温情;理,表达的是双方自愿,绝不勉强之理,考虑到的是契约精神需要双方自觉遵守的原则。这就把面子和里子,感情和理智都有机结合起来了。具体说来,收入全书的1194件契约,每一件不仅是规范的应用文,还是漂亮的书法作品。书写相当规范,字体圆润漂亮;文脉代代传承,格式变动很小;用词优雅委婉,表述准确无误;中人德高望重,说话一言九鼎。传统的人文精神,乡土的文化底蕴,各具风采,扑面而来。翻阅这些带着岁月风尘的契约,就如同掸去一个个宝瓶上面的尘埃,让我们看到的是一 页页浸透着前人智慧的真实图画。仔细揣摩其中的话语,似乎还能看到许多家庭的人们正在做什么,想什么。说它是乡土寿阳的“清明上河图“,一点都不为过。这何止是在和前人对话,更多的是让后人身临其境,感受到了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。突出表现在:第一,具备法律效应。如,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十一月初五立的一份李成荣包揽契。因为李成荣的小舅子偷到杨坡村杨德四件衣服,被村中人拿住,李成荣立揽契为证,出面担保,“村中以后再有失盗者,李成荣一面承担。”保证其小舅子如果再犯,“由家人自行处死,与杨坡村人无关,同母亲王氏为证。”并由五指手印盖章。这是全书所有契约中唯一一份盖有五指手印的契约。仅仅偷了四件衣服,就提出如果再犯,“由家人处死”的庄重承诺。由此可看出,家法之严厉,亲情之珍贵,义气之担当,管教之严格,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小舅子再犯,杜绝不良行为。同时,也对村里其他人有着示范效应。这样的“法”由家法来体现,今人实难想象,但在当时,应当还是有积极作用的。表明这是一个不徇私情的好家庭。再如,光绪二年三月十五日立的王德善揽工契,明确写清了房屋修缮的各种细节,包括工程方位,拆墙数量,烂砖、瓦、土等应放位置,主家需提供的石灰、砖瓦,还有泥墙标准,应付工钱等。这其实就是一份详细的工程合同。财产纠纷向来是比较棘手的麻烦事,处理不好,极易引发矛盾,即使到现在,也有不少因此引起上访行为。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,张广荣卖坟中松树契,就充分说明这一点。因坟中松树两株,正北西边大树一株,系张义中分定之树,但是,张广荣伐卖。导致张义中之妻下县告状。这一来,事情就闹大了。为平息矛盾,经村中父老说合,“将正北东边小松树一株,內有广荣股份,卖于广荣,作价二千三百文,此钱当交不欠。此后坟中松树与广荣无干,永远杜绝葛藤。空口无凭,立约为证。”并有四位中见人作证。很显然,这就是一份富有成效的民事调解书了。不可否认的是,这里边还有两大因素不能忽视。一个是村人说合,翻遍全书,每件契约都有说合人,这其实就有现在我们常说的协商民主意识了,因为协商民主就发端于我国,植耕于中华文化传统土壤,具有顽强的生命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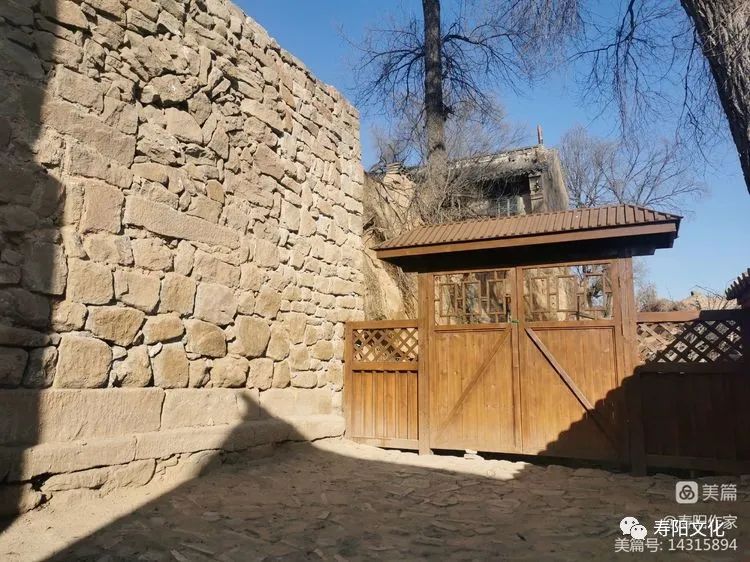
再一个就是中见人(有的契约体现的是保人、族人,还有代笔人,解放后多数为村干部),目的是增强契约的说服力和公信力,具有很强的舆论力量。一般来说,能做说合人和中见人、或保人的,都是村里有头面的人物,其特点是在村里都有威望、能服众,公道正派,有议事能力和办事水平。本书中,最多的一件契约,曾出现过九位中见人。我们现在说的乡贤治村,其实,也正是特指这一类人。第二、凸现道德约束。良好的民风村风家风都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,三者不可分割。这其中,道德的约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一书中指出,“道德观念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。它包括着行为规范、行为者的信念和社会的制裁。”“孝、悌、忠、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。”由此可见,父子之间,作为子一辈,就要体现孝道,夫妻之间,作为双方,就要体现互敬和睦。特别是作为双方的大人,对夫妻间闹意见,区分相当严格,教育惩诫也很严厉。关于这一点,本书的有关契约说明十分突出。如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三号赵振宜善后契,因婚姻家庭不和善后,就是明显一例。起因是赵振宜的侄女出聘于王亲家寿林家中,与夫不和,就在自己家中多住了几天,弄出了口舌是非。处理结果就是,“今情愿送婆家与夫主和睦度日,日后若有寻死短见之事,与己无干,决不闻问,空口无凭,立此凭据为证。保人赵履寿。”从这份契约的语气来看,非常坚决,说明对侄女的行为很气愤,而且还断了侄女的后路,“日后若有寻死短见之事,与己无干,决不闻问。”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到,这位侄女看了以后,再不敢和丈夫“不和”了。至于离婚,那更是不敢想的事情。农耕社会的婚姻之所以稳定,离婚率之所以极低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妇女社会地位低下,经济难以独立。作为妻子的一方,是没有权利提出解除婚约的,那会被人认为是大逆不道,所以只能是由男方来“休妻”。当然也不能否认,舆论上也有离婚是一件丢人的事的氛围。但至少也说明,传统婚姻道德的力量对妇女追求幸福的束缚和精神折磨。联系到现代社会,离婚率居高不下,对待婚姻过分草率,单身者日趋增多,而且城市要远远高于农村,甚至是由女方主动提出“休夫”,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,妇女地位有了很大提高,经济独立性增强,人口流动加快,由农村的熟人社会,变为城市的生人社会,没有了道德约束,也就不怕人笑话,把离婚看作是追求个性解放所致,说明传统的道德作用正在降低。 第三、延续生命香火。多子多福,人丁兴旺,后继有人,子孙孝顺,是漫长的农耕社会体现的家庭兴旺的标志。当一个家庭真的到了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的境地后,主人也就在人前抬不起头了。这个时候,延续香火的唯一办法就是“过继”了。收入本书的三件过继契,时间都在民国年间,对于继承的土地、房屋、家具等财产和应该承担的义务(养老送终)等,都有明确规定。不仅都有说合人和代笔人,其中一件还有家长,另一件还有家长和村副、闾长。由此可见,涉及顶门立户的大事,既有“人”,又有“产”,这就要比其它契约慎重得多,也神圣得多。透过字里行间,完全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那种庄严肃穆的场面。这和当代社会的“丁克”家庭,生育率一再降低,又形成了照明的对比。“延续香火”的观念,早已经渐行渐远了。是时代的进步,还是经济压力增大所致?大概都有吧。